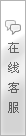济宁商标_济宁商标注册_济宁商标查询_济宁商标代理_济宁专利_济宁专利申请_济宁国际商标注册_济宁马德里商标注册 - 济宁雨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近年来,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依法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以遏制此类行为。其中,恶意提起商标诉讼尤为典型。[1]这种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不仅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严重背离了保护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立法初衷,极大浪费了司法资源。
为规制恶意诉讼行为,早在21世纪初,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曾对此展开立法探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关于恶意诉讼问题的研究报告》。2006年《专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A10条第二款规定了恶意诉讼的定义和法律后果。2019年《商标法》修改,新增“恶意提起商标诉讼”司法制裁条款。2023年《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了恶意诉讼反赔制度。
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初现雏形,但立法一直未明确其定义和构成要件。当前研究也多侧重于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机制和责任承担,对具体识别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识别商标恶意诉讼、厘清商标恶意诉讼与其他相似概念的界限,是准确适用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的前提。识别标准不明、边界不清将导致制度无法完全发挥效用,难以应对商标恶意诉讼愈演愈烈的现实困境。故对商标恶意诉讼的边界与识别问题之研究 , 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商标恶意诉讼的司法检视
虽然商标恶意诉讼规制立法尚不完备,但司法实践率先进行了探索。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二级案由 “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下设“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希望能总结审判经验。[2]
通过检索“威科先行”裁判文书库,筛选得样本198个。初步整理分析得:(1)成立商标恶意诉讼的占比较低,15篇文书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占比7.58%。(2)法院说理相对薄弱。仅33篇结合案情详细分析了恶意诉讼的定义、性质、构成要件等,占比 16.67%。(3)商标恶意诉讼边界不清。当事人诉讼或辩护理由中多存在将恶意诉讼与重复诉讼、批量诉讼、妨碍诉讼、虚假诉讼等概念混用的现象,法院说理部分也存在此问题。(4)商标恶意诉讼之定义、性质、构成要件等分歧很大。定义上,仅24篇文书展开说明,经对比分析得13个不同版本,分别在行为目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损害后果上存在不同观点。性质上,认为属于侵权行为的有22篇,属于滥用权利的有18篇,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2篇,属于妨碍诉讼行为的有1篇。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恶意诉讼的定性并非互斥,如有的文书认为恶意诉讼既是侵权行为,又是滥用权利行为。构成要件上,有的采用侵权责任四要件标准,有的另行确立标准,但多强调“恶意”。
可见,解决商标恶意诉讼的边界与识别问题迫在眉睫。一方面,边界不清将导致商标恶意诉讼与其他相似概念的混用、误用,进而导致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在适用时偏离立法本意,不利于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另一方面,认定标准不明使得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无所依凭,认定标准不一,无益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和维护司法公信力。确定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就是将商标恶意诉讼与其他相似概念区分开来的过程。同时,商标恶意诉讼构成要件的确定又深受其本质的影响。故下文将首先明确商标恶意诉讼的本质,其次提出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以建立相对统一的商标恶意诉讼识别规则,促进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的解释与适用。
要解决商标恶意诉讼的识别问题,需先确定商标恶意诉讼这一概念的内涵。而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换言之,本质属性深刻影响内涵的确定。故把握商标恶意诉讼的本质有助于解决商标恶意诉讼的边界与识别问题。当前,有关商标恶意诉讼本质问题存在三种学说,即侵权行为说、不正当竞争说和权利滥用说。侵权说认为商标恶意诉讼是侵权行为,满足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应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3-5] 不正当竞争说认为,商标恶意诉讼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主要由竞争法规制。[6,7]而权利滥用说则认为恶意诉讼的本质是权利滥用行为。[8]
(一)权利滥用说的证成
商标恶意诉讼本质是权利滥用行为,而非侵权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权利滥用”起源于罗马法,是法律对私权行使的限制。[9]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也规定禁止滥用民事权利。一般认为,权利滥用是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10,11]商标权人以损害相对人利益为目的,明知无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仍提起诉讼的,其商标权行使行为就违反了诚信原则,构成商标权滥用。而侵权说和不正当竞争说混淆了行为评价与行为本质。行为可由多种法律制度各有侧重共同规制,但受何种制度评价并不决定其本质。商标恶意诉讼可从不同角度受侵权制度和竞争法律制度评价,但这不意味着其本质就是侵权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否则其本质上是垄断行为、犯罪行为等。
权利滥用说更符合立法目的。权利滥用制度是权利行使规范,通常通过对权利人施加不利以避免权利滥用行为发生;而侵权制度是权利救济规范,主要以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的方式实现救济受害人的要旨。[12]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旨在制止商标恶意诉讼,从源头上规制恶意抢注行为。[13]故该制度是权利行使规范,而非权利救济规范,否则无法解释《商标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商标恶意诉讼司法制裁条款。同时,商标恶意诉讼若以侵权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本质,则势必以损害后果为构成要件,导致制止效果滞后和规制范围过窄的问题。[14]
(二)权利滥用说的澄清
支持权利滥用说的学者多认为恶意诉讼是对诉权的滥用。[15] 但实际上,滥用的应当是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而非诉权。以属于原生抑或派生为标准,权利可分为原权与救济权。救济权是当事人为救助其受侵害的原权而产生的实体权利。[16]当商标权遭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商标权人可行使商标权派生出的救济性请求权,直接请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若其请求权得不到实现,权利人可诉诸国家公权力保护,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以实现其救济性请求权。当然,权利人也可直接起诉。这种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利就是诉权。[17]换言之,行使诉权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救济性请求权。提起商标权侵权诉讼,程序法视角下,是行使诉权的行为;而实体法视角下,则是行使救济性请求权的行为。但由于商标恶意诉讼不宜局限于诉讼行为,也包括其他行使救济权的行为,故商标恶意诉讼更宜认定为商标权救济性权利滥用行为。
四、商标恶意诉讼的具体识别
识别是规制的前提。明确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和表现形式,有助于准确适用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
(一)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
基于商标恶意诉讼的本质是商标权救济性权利滥用行为,其识别标准可从权利滥用的角度展开。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滥用是不正当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18]相应地,商标权救济性权利滥用是不正当的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故对商标恶意诉讼之构成要件的分析,可以从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和行为的不正当性两个部分展开。
1.客观要件: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
商标权救济性权利是商标权遭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产生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行为不限于提起诉讼,也包括向相对人发送侵权警告[19]、向第三人或行政机关投诉侵权等。[20]恶意诉讼虽采用“诉讼”的表述,但不宜限为《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诉讼,目的性扩展解释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旨在制止借诉讼牟利的行为,从源头上制止恶意商标注册。[21]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能否达到牟利目的,而非行为方式为何。权利人采用非诉讼方式同样可达到向相对人“敲竹杠”等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司法或行政机构程序的悬而未决可能延迟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在其他方面对其造成损害 [22],关键时刻向第三人投诉侵权亦可能给相对人造成产品下架等损失。此外,行为人将“维权行为”向社会披露,就有可能使相对人陷入商誉危机。上述损害均可成为行为人“敲竹杠”之依凭。若将非诉讼方式排除在规制范围外,可能导致制止借诉讼牟利之立法目的无法完满实现。在“CPU”商标纠纷案[23]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请求行政机关查处等恶意维权行为构成商标恶意诉讼。
2.主观要件:行为人具备“恶意”
商标恶意诉讼的不正当性体现为行为人明知其商标权实质无效仍行使商标权救济性权利的“恶意”。传统民法将行权目的作为不正当的判断标准,但该标准不自足,其适用有赖于以立法目的为判断标准所作出的利益衡量。[24]当商标侵权行为成立时,支持商标权人之行权行为并无异议。但若商标权侵权行为不成立,则相对人就有受到不合理救济请求侵扰的可能性。依据侵权行为不成立的原因,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商标权未受侵犯时,由于商标侵权纠纷极为复杂且具有较高的专业壁垒,当事人通常难以判断商标权是否受到侵犯。为了避免打击商标权人维权的积极性,促进纠纷解决,应当优先支持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其二,商标权虽有权利外观但实质无效时,相对人不受不合理救济请求侵扰之利益与权利人对所享有商标权之权利外观的信赖利益会产生冲突。若禁止行使救济性权利,则可能动摇潜在注册申请人对商标注册取得体制的信赖;若不予制止,则相对人将承受救济请求所致损害。但后者仍可通过商标无效宣告程序和行政诉讼及时止损。因此,只有当权利人对其商标权之权利外观不具有信赖利益,即明知其商标权实质无效时,才是制止行权行为的唯一情形。
主观“恶意”应至少为故意,不包括过失。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多认可此观点。商标权无效有两种类型,先天型与后天型。前者是指,商标注册申请时不符合条件,包括恶意注册的无效和非恶意注册的无效。后者是指,商标注册申请时符合条件,但后续使用过程中,因商标丧失显著性、三年未使用等原因而无效。对于先天型无效中的恶意注册无效,权利人恶意明显,自不待言。但对于先天型无效中的非恶意注册和后天型无效,判断商标是否实质无效有赖于专业知识,权利人对于商标注册结果存在信赖可能性。只有当权利人明知商标权无效,才有必要禁止其行使救济性权利;否则将无形之中弱化商标权正当行使,不利于公民救济性权利的保护。
综上所述,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可归结为:客观上,该行为是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主观上,行为人具备明知商标权实质无效,仍行使商标权救济性权利的“恶意”。
(二)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
当前有关商标恶意诉讼具体包括哪些表现形式存在争议,主要涉及重复诉讼型、无据诉讼型、恶意串通型、妨碍证据型、不当取得型。结合前述商标恶意诉讼之本质、构成要件,本文认为,当前只有不当取得型是商标恶意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
重复诉讼型、无据诉讼型、恶意串通型、妨碍证据型均非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首先,重复诉讼型的典型形态为,权利人于不同法院针对不同零售商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并形成批量诉讼。[25]因权利人针对不同侵权主体提起诉讼属行使权利之应有之义,无“恶意”一说,故该行为并不符合商标恶意诉讼的主观要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对重复诉讼已有所规定,《商标法》不宜另立门户。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该条过于注重形式审查,导致禁止重复诉讼制度形同虚设,并建议依据利益衡量采用扩张解释。[26,27]因此,即使有必要予以规制,也宜采用民事诉讼规范内的方式,不应作为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其次,无据诉讼型,即在权利未受侵犯的情况下,权利人明知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提起诉讼的行为,也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不是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当权利未受侵犯,商标权并未派生出救济性权利,权利人并无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不符合商标恶意诉讼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商标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当事人往往难以确定权利是否受侵害,将该行为认定为商标恶意诉讼可能不当阻吓权利人寻求救济的积极性。即使相对人因此承担了律师费用等成本,也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之精神,由法院支持无过错方提出的赔偿合理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弥补。比较法上,《美国法典》第15编第1117(a)条亦采用相同做法。[28]再次,恶意串通型和妨碍证据型亦不属于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恶意串通以诉讼损害第三人利益和伪造证据等行为显然不属于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此外,依体系解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已将此二类行为认定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并施加相应责任,无须由《商标法》另行规定。
不当取得型是商标法恶意诉讼的典型表现形态,具体指行为人恶意注册取得商标权后,针对特定对象提起诉讼或以诉讼相威胁,企图向该商标实际使用人“敲竹杠”以获取不正当利益。首先,该行为符合商标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客观上,权利人针对特定对象提起诉讼或以诉讼相威胁的行为,属商标权救济性权利行使行为;主观上,行为人通过恶意注册取得商标权,明知所获商标权虽有权利外观但实质无效。其次,将该行为作为商标恶意诉讼的表现形式,符合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的立法目的。2019年《商标法》新增恶意诉讼司法制裁制度,主要是为了“从源头上制止恶意申请注册行为”,打击“为转让牟利而大量囤积商标的囤积注册行为”。[29]2023年《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引入恶意诉讼反赔制度,也强调应对“不当行使和滥用权利现象时有发生,借诉讼牟利甚至恶意诉讼的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困境。[30]在“优衣库”商标纠纷案中,指南针公司不当取得涉案商标,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给优衣库公司,未果后又以侵害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起诉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31]表面上,指南针公司是在正当行使商标权救济性权利,实际上,该公司大量申请并囤积注册商标,并通过商标转让、诉讼等手段实现牟利,主观恶意明显,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损害了相对人利益,应受商标恶意诉讼规制制度调整。